行在光中
我与北村有个约
文/子玉

律法只能因人的罪而审判,然而信仰却能使人的灵魂甦醒、知罪、悔改和重生……
我为中国文坛出现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而欣喜,并期待更多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出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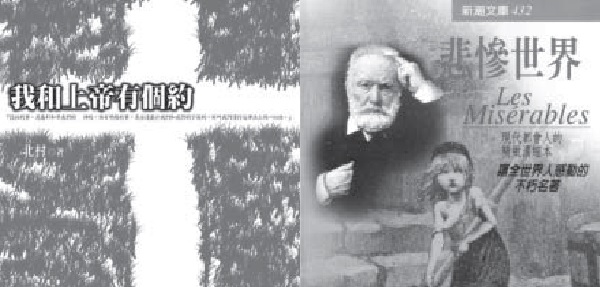
出国多年,閒暇时喜欢看中文小说,内心仍关注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。近二、三十年间,中国大陆产生了许多部优秀的中、长篇小说。信主之后,渐渐悟出好的作家仅仅具备正直豁达的人品、悲天悯人的心灵、饱学博识的素养、高超干练的文笔是不够的,若缺乏信仰支柱,作家的灵魂视野便存在残缺,即使持守著文人的良知和使命,仍然写不出人性中的崇高和永恒。
北村,以中国先锋小说家享誉中国文坛。久闻其人为一名基督徒,从书名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宗教小说。我满怀期待地捧起了这本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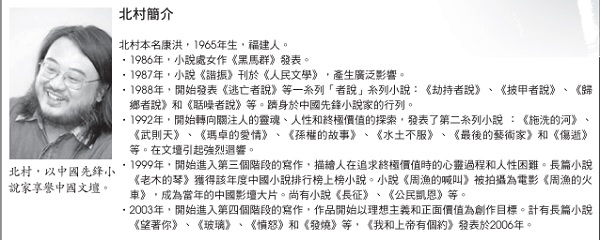
黑暗使人绝望
这部小说情节错综複杂,设计巧妙,跌宕起伏。故事以现今中国社会为背景,围绕一起城市的兇杀案,将这个城市中各个阶层中,上至市长、教授、记者和商人,下到农民、妓女、夜总会女郎和兇手等人带到读者面前,用叙事手法描写人性的醜恶与善良、堕落与拯救。
陈步森是小说的主人翁,一个三十岁的无业遊民,靠偷盗抢劫苟且偷生,后因参与一起兇杀案,被捕并受到法律对他死刑的判决。
就以上对此人的介绍,读者难以给予陈步森同情,什至会断定他不过是个罪有应得的人渣而已。然而当我们随著作者的笔触走近陈步森的心灵,会发现他和《悲惨世界》里的冉阿让(Jean Valjean)一样,本性纯洁善良。陈步森的父亲身体残疾,因无力生存而沦落成贫民,家庭的破碎,将少年的陈步森推向生存的险境。被父母抛弃后的陈步森,在求生的困境中挣扎过、努力过,命运的坎坷和遭遇一而再,再而三地将这位少年推向黑暗的边缘,最终他走到了社会对立面。
小说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醜陋和败坏,以及社会的黑暗。在巨大的黑暗笼罩下,人与人之间因缺少爱和真诚,因不能饶恕和宽容待人,或因仇恨和报复而施害于人。在置身于黑暗又製造黑暗的漩涡中,所有人都成了黑暗的受害者兼施害者。
人物中并非只有陈步森是黑暗所吞噬的牺牲品。市长陈平,城府世故,随波逐流,丧失正直,因腐败被追查,陷于恐惧而不能自拔;廉洁的副市长李寂误被残害,妻子冷薇受刺激而疯;主谋兼主犯胡土根是为其受害而亡的父母报仇,而用暴力向社会挑战。
冷薇身为被害人,因不能饶恕仇人兼恩人的陈步森,心灵受到痛苦的煎熬;同时因恨而被扭曲,并因殴打学生而失去教职。著名的道德学教授陈三立精研儒学,涉猎佛道诸论,却是道貌岸然,对乞丐缺少怜悯、对人缺少同情和尊重,被婚外情人千叶设下陷阱而身败名裂……。活在黑暗中的人是罪的奴僕,是在罪的綑绑和辖制之下;黑暗带给人的是罪性、是堕落、是毁灭、是绝望。
光明击碎黑暗
如果到此为止,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便同许多作品一样,停留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层次上,停留在深掘人的慾望和隐私里。于是无论技巧如何天衣无缝,描写如何惊心动魄,结论只有一个:生命无非是在黑暗中相互碰撞、相互碾压、相互残杀,是没有盼望、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。
黑暗的出路在哪里?
「窗外曙色微茫。行刑的时间到了。苏云起和陈步森要分别了。……苏云起说,记住,等一下不管遇到什么,一定要朝著光明的地方去。陈步森知道他是说枪响之后的事,眼泪一下子湧出来。」 1
苏云起是何人?作者笔下,他扮演了《悲惨世界》里卞福汝主教(Bishop of Digne)的角色。他大学毕业后经商,赚了很多钱,也曾经堕落。信主之后变卖资产,成立公益慈善机构─社会公益辅导站,从事心灵拯救工作。
那时的陈步森,已在苏云起的带领下找到了信仰。找到信仰后的陈步森,如同在黑暗中见到光明。他不仅在内心深处彻底地认罪悔改,从因犯罪带来的痛苦和恐惧中,以及死亡的阴影中释放出来,因著与神的连接,恢复了人性本该应有的高贵品格,即仁爱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
首先,多年对母亲的怨恨从他内心除去,取而代之的是爱的恢复。对罪的认知、彻底的悔改,使他为了帮助受害人妻子冷薇从精神病症中得以恢复,不惜冒著自己落入法网的危险,判刑之后,为挽救冷薇的生命,捐献出自己的器官。
律法只能因人的罪而审判,然而信仰却能使人的灵魂甦醒、知罪、悔改和重生。虽然陈步森在肉体上最终还是得到法律的审判,死亡结局令人悲哀,但是他内在生命改变的见證使许多人的灵魂开始甦醒,让人们藉著他看到了光明和盼望。
故事结束了,哀伤在宁静中渐渐散去,化成一片安祥和宁静。「冷薇望著窗外,好像看到了远山之上的天空。她想,此刻,他已经坐在天上了。……在这样的宁静中,从地上捡起一根草都是美的。」2
诠释黑暗和光明
圣经新约中,多处论到光明和黑暗,譬如:「你们从前是黑暗的,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,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,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」(以弗所书5:8-9)
在读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时,总是联想到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,因为两者有许多共同点:描述了下层人民的苦难,用现实主义的手法,用文学的形式,诠释了黑暗和光明。《悲惨世界》是讲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。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是讲一个死刑犯认识神之后从罪性里解脱达到自由的故事。
在《悲惨世界》里,雨果借助卞福汝主教之口,说:「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,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。」3 当光照在并充实冉阿让的全部心灵时,他淌著眼泪,泣不成声。「那是一种奇特的光,一种极其可爱同时又极其可怕的光。……那种光的明亮是他从未见过的。他回顾自己醜恶至极的生活,卑鄙不堪的心灵。」4
在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里,作者藉著苏云起说:「坐牢只能限制你做怀事,不能除掉你心中的罪,只要你从内心认罪,你的罪就被赦免。」「陈步森心中的堤坝终于溃决了,一下子哭出来:我愿意认罪……」5 陈步森在给冷薇的信中说:「我现在才明白,我是按圣洁的形像和样式造的,……我高贵是因为我是按圣洁的形像和样式造的,……可是,我却在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活了三十年,……」6
当然,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,并非说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和《悲惨世界》一样,同是经典传世之作。
从文学角度省思
我个人认为,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的作者注重人物心理剖析,挖掘人心灵深处的暗角,藉著作品中的人物达到了传扬和解读圣经教义的目的,这是应该被借鑑的。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。
作品传达一个信息,世无完人,每个人都是罪人,而每个人犯罪都有缘由。但要给每个人物犯罪的缘由从心理上一一解释,除了陈步森、冷薇和陈三立之外,还包括辅导者苏云起、市长陈平、罪犯胡土根、妓女千叶等等,面面俱到就显得笔墨不足。
靠人物的大量陈述,人物显得缺少个性特徵。大段的思想论述,难免说教的痕迹显而易见。注重人物的思维表现而缺少形体表现,过多地依靠语言表现人的思想会让读者感到乏味。其实情节的发展中,人物的一颦一笑都能表现人的思想,没有诠释的行为同样也能反映心理。国画讲究留白,文章留给读者空间同样重要。
用TELL代替SHOW,即作者的陈述代替故事本身说话,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面缺少作者和读者的互动,故事会缺少立体感。倘若增加场景的铺垫、人物外在的描写,以及通过人物对话处理,会不会使人物更加活灵活现、人物性格更加丰富饱满,思想脉络自然就水到渠成?
身为一个工程专业的普通读者,我对此书的见解不一定全面,见仁见智吧。当然,挑了诸多不是并非否定作品。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无疑是一部深刻、光明、优秀的作品。我为中国文坛出现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而欣喜,并期待著出现更多的基督教文学作品。
以基督文化做底蕴
每个人受到生活环境和经历的局限,必然对世界的认知匮乏,基督徒也是如此。文学作品可以间接地帮助我们认识人性、认识社会,弥补我们经历上的不足;而优秀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,更多地认识神,同时了解自我的残缺。
譬如说,生活的环境中和阅历里,不曾近距离地接触过贫穷和罪犯,我对那群体是陌生的。妓女、罪犯和歹人在我心目中都是脸谱和符号,与堕落、暴力画上等号。正因没有生活在社会的底层,正因生活的平顺和富足,正因与生俱来的一些良好品性,便更容易表面上谦卑善良正直,内心隐藏著骄傲和自以为义,从而难以将罪和悔改与自身联系起来。
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让我对罪的认知、悔改的功效和得救的确据有更多的认识。书中的陈步森,帮助我们了解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上的罪犯,何以得救而与耶稣同在乐园里,为何圣经中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。
掩卷沉思:什么是人的爱,什么是神的怜悯和慈爱;什么是人的律法,什么是神的宽恕和拯救;什么是活在黑暗中的结果,什么是行在光明中的生命。(本文图片摘自网路)
註
1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,台北,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 478-479页。
2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,台北,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 480页。
3. 雨果,《悲惨世界》(上),中国,大众文艺出版社,世界名著宝库系列丛书,15页。
4. 雨果,《悲惨世界》(上),中国,大众文艺出版社,世界名著宝库系列丛书,99页。
5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,台北,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168页。
6. 北村,《我和上帝有个约》,台北,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,2006年,407页。



 作者小档案
作者小档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