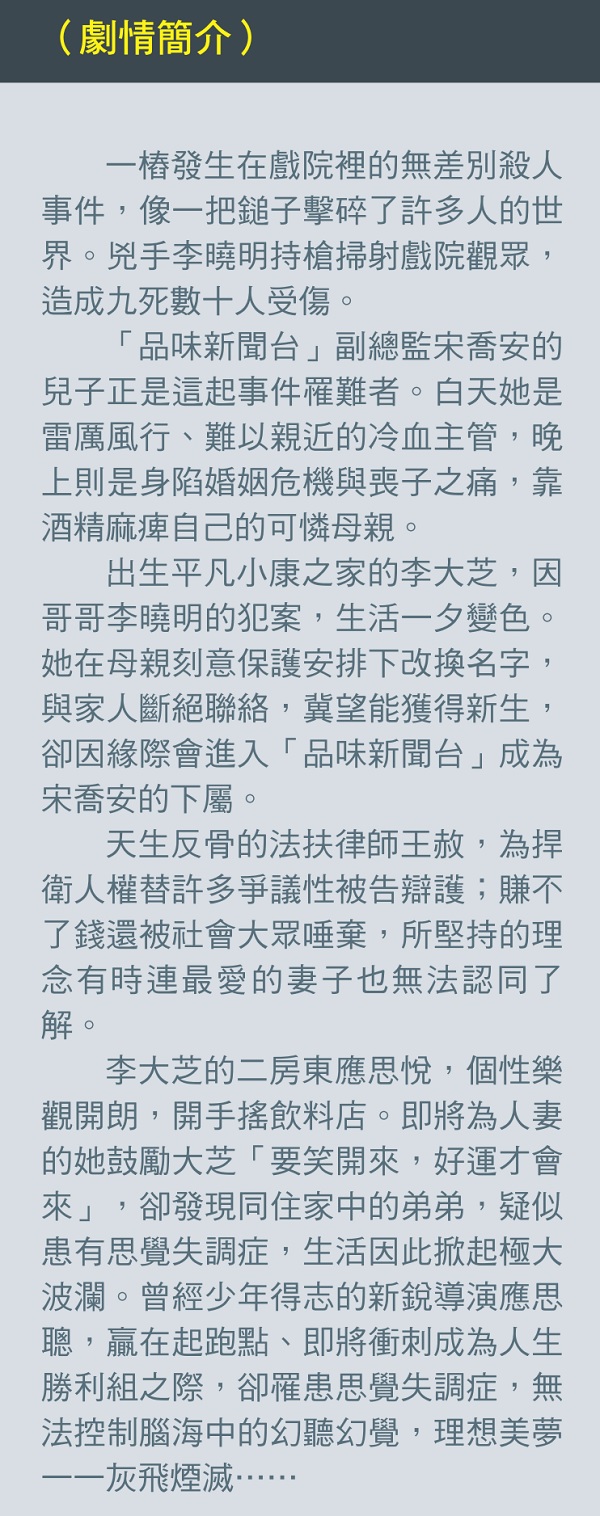忽远忽近之间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观后感
文∕滋恩

「世界崩裂,我跌入深渊。黑暗里,光是一条细细的线。我向上伸手,却抓了个空。原来,暗与光的距离,比我想像的遥远。」─《攀爬》‧佚名
2019年台湾公共电视出品并首播的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(以下简称《与恶》),描述无差别杀人事件(或称「随机杀人」)过后,处于不同立场与身分的人们,如何在现实困境中挣扎,努力拨开层层阴霾迷雾,看清彼此与自身的面貌,以期达到救赎与和解的故事。
《与恶》的故事,提供观众一个深思的议题:我们与恶的距离,有多远?当我们试著丈量与恶的距离之际,是站在对立面遥望?还是处在同心圆里努力与之抽离?

▲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中,彷彿每人都拥有手执石头的权利与权力。
手中的石头
剧中每集开头都以一则新闻报导作为序幕,紧接著拖曳出一连串社群平台对此则新闻的留言回响,最后纷飞的文字碎片慢慢拼凑出剧名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─无论是所谓的「键盘酸民」,还是「网路正义魔人」,在这众声喧哗的自媒体时代中,彷彿每人都拥有手执石头的权利与权力。
然而,谁有资格拿起石头?扔掷的动机是什么?身心俱创的受害者、失去挚爱的被害者家属、自卑愧疚的加害者家属、铁面无私的执法人员、坚守司法正义的律师、自诩社会良心的媒体工作者……是否任何奉公守法、心存正义的「好人」,就拥有口诛笔伐的条件,能为正义发声?扔出石头的刹那,瞄準的目标,是罪人?是他所代表的恶?还是从罪人身上看到自己那隐而未现的恶?
哲学家沙特(Jean-Paul Sartre)曾说:「邪恶不单只是表面上的样子。」当恶人被法律定罪后,是否代表「邪恶」就被剷除了?若因应罪的终极行动,仅只于扔掷石头在罪人身上,岂能根除罪的源头?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,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」(约翰福音8:7)面对高喊要求正义的群众,耶稣的话如利刃划开了虚伪的表象,露出赤裸裸的真相:没有人是无罪的─主若察究罪孽,谁能站立得住?
圣洁公义的主,选择道成肉身来到充满罪恶的人间。祂并不定我们的罪,反而自己成为替罪的羔羊,流血捨命,赎回本该被石头打死的我们。雅各书说「怜悯原是向审判誇胜」,惟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显现的爱与饶恕,才能使我们不继续在罪的漩涡中打转,真正脱离恶的挟制。

‧2019年台湾公共电视出品的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,描述无差别杀人事件过后,处于不同立场与身分的人们,如何在现实困境中挣扎,以期达到救赎与和解的故事。
自媒体时代的基督徒
现今媒体资讯氾滥,新闻事件如海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所谓的重大新闻事件往往只在记忆的海滩停留片刻,就被另一波浪潮席捲而去。「将事隐祕乃神的荣耀,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。」(箴言25:2)如何下工夫深度探索、观察,从属灵的角度来剖析事件背后的人性,是基督徒要不断操练的功课。
媒体呈现事件表象,著重于报导事件本身,却常忽略了事件核心中的「人」。是怎样的一个人,会披上堕落的斗篷、戴上邪恶的面具,犯下人神共愤的罪行?有人的地方就有事,人物推动著事件的进行。为强调大众有「知的权利」,并即时带来「资讯的更新」,事件里人的脸孔标準化、形象平面化,什至个性标籤化─失去人性温度,只求传达资讯,是否真能达到新闻诉求的目的与原旨?是否带给读者「知」的意义?
当点阅各类充斥网路的新闻资讯时,心中丈量与平衡的标準从何而来?当转发或按讚,大推必看好文、重要新闻报导时,出发点源自何方?如果耶稣是我个人自媒体平台的总监,每日呈现给祂的简报,何者为头条?什么值得深入报导?

▲自觉握有终极正义感的王赦律师,为杀人犯奔走努力,却无法找到恶的癥结并解决其带来的结果。
剧中饰演为死刑犯极力奔走的律师王赦,入围金钟奖的演员吴慷仁,本身并不支持废死,但为了揣摩诠释剧中角色并深入其内心世界,他花很多时间与不同立场的人对话,试著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帮助在大家眼中十恶不赦的人。
在这过程中他发现,无论是反废死的律师或是相关团体,真正致力坚持的是在「爬梳被资讯媒体忽略简化、从未深度报导的犯罪者背景,他们希望让社会重视背后潜藏的问题:可能源自于精神疾病、可能来自家庭的养成,这些所谓的被社会统称的『加害者』,他们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。藉由不断追寻『为什么』,理清这些人的家庭、求学过程等脉络,他们的重点不在于帮助犯罪者脱罪,而更希望凸显背后的原由;找到它,拉出来被大家检视与讨论。毕竟这不会是惟一的案例,未来还是可能有其他类似案件发生,因此如何『预防』,或许更需要被重视。」註
在新闻容易取得、讯息频繁更新的网路时代,人们容易囫囵吞枣地吸收各种资讯,草草吸收后便马上给出结论─如果一位演员,为了好好扮演他的角色,都能如此下功夫,放下自身的预设立场,和与自己持相反意见的人对话互动,基督徒是否更需有这样的同理心与对话的意愿,愿意踏出同温层,试著去了解「非我族类」的痛苦与挣扎?

▲媒体呈现事件表象,著重于报导事件本身,却常忽略了事件核心中的「人」。
面对苦难的同理心
剧中的「思觉失调症」患者应思聪,饱受幻觉幻听之苦,原本大好前程因病崩塌毁坏。他曾流著泪问道:「为什么是我?」杀人兇手李晓明的妈妈,也曾无助地问自己:「我每天睡不到两小时……早想、晚想……到底是哪里把小孩教坏了……是我们太忙太自私都没空跟小孩聊天说话,所以会教出这样变态的杀人魔?」
面对人生的苦难与矛盾,我们或许不会质疑受苦者「是他的父母或是他自己犯了罪」,但会不会因为有圣经的标準答案,有神学的完整理论作基础,就不觉陷入「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,说『平安了!平安了!』」的光景?
你我都曾陷在「恶」的泥沼中,是谁助我们拉开了与「恶」的距离?在如此的跨越中,我们所经历的是怜悯与恩慈?还是定罪与刑罚?
基督徒以真理为基础来分辨善、恶、是、非。在「分别为圣」的同时,是否也愿意仿效耶稣,走进人看为恶的群体,以怜悯和恩慈贴近他们的心?光进入黑暗,不单是为了伸张公义,更是为了驱走黑暗,将在幽暗中的人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我们是否愿意搭起倾听与对话的桥樑,什至成为多走一里路的陪伴者?
基督徒与恶的距离,不见得比未信者遥远。在一个需要不断与罪恶相争的世界,《与恶》一剧里精神科医师一骏曾说:「这是一个众生皆有病的社会」,并提到了「病识感」这个专有名词,就是指精神病患本身不觉得自己有病,因此拒绝就医或服药的心理状况。没有病识感的患者,不单使自身的病况加重,什至也可能拖累身边家人亲友。
有病需要就医,有罪如何处理?我们对罪,有没有「罪识感」?会不会因为信了耶稣,得到进入永生的门票,就像龟兔赛跑中的骄傲兔子,躺在树荫下打盹,而忘了我们在世的日子?或是得像一个坚持到底的马拉松选手,不松懈不偏倚地朝著标竿直跑?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警醒,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,面对罪恶的引诱试探,可能全面缴械而不自觉。

▲对话是往前踏步的开始,也是饶恕心路历程的起步。图为剧末宋乔安夫妇与凶手李晓明的父母的谈话剧照。
当我们不再属于世界
《与恶》的导演林君阳及製作人林昱伶在接受媒体访谈时都提到,剧名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的重点在于「我们」,而非「恶」;「我们」,才是本剧的核心。这个世界是由无数个「我」所组成的,「我们」共同描绘建构出这个世界的黑白形色、曲直轮廓─世界的善恶你我或多或少都有分,什至彼此影响牵制。
基督徒是神所分别为圣的选民,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来看善与恶?从何种角度切入来「入世却不属世」?基督徒的「我们」,与世界的「我们」,有重叠的时候吗?这是一道可以一分为二的界线,还是一条必须不断拔河的绳索?在面对人性黑暗与生命悲剧时,我们所处的道德或信仰制高点,是否能帮助我们超然以对?
纵使有「罪识感」,若离了主,没有基督的灵在里面,我们很可能也会犯下要被扔石头的罪。人世不似棋盘黑白分明,是非对错都有自己的位置。「在我里头,就是我肉体之中,没有良善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,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」(参考罗马书7:18)

剧中的宋乔安,封闭自己,躲避恶所带给她的伤痛,却不觉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丈夫和女儿。自觉握有终极正义感的王赦律师,为杀人犯奔走努力,却无法找到恶的癥结并解决其带来的结果。若靠著自己,我们与善恶的距离,往往忽近忽远、若即若离。这个世界里,恶的阴影势力无所不在,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完全脱离它的挟制。
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」─因著哥哥犯下的恶,不断躲避掩藏,在夹缝中求生的李大芝,接受应思悦的关怀与接纳,学会绽颜欢笑,面对不堪的过去。社工乔平,面对思聪的哭诉:「为什么是我?」温暖回应:「可能因为你比较勇敢吧!」带给他站起来的力量……
「有一个人改变,过往的互动模式就会变动……很难说会变好或是更糟,但通常会建立新的互动方式。」剧中乔安与昭国的婚姻谘商师曾如此说。能真正将人从黑暗拉向光明的,惟有那双向世界伸出的钉痕手。但你我都可以成为那将人拉近与光之距离的推手。距离,在同情与定罪之间。距离,在怀恨与饶恕之间。距离,在贴标籤与撕标籤之间。距离,在认罪与赦罪之间。
看似乐观无敌的应思悦,承认自己也有害怕无助的时候,却告诉自己仍要「笑开来,好运才会来。」她告诉李大芝,「看得见的东西不用相信,看不见的东西才要相信。」忽远忽近之间,有时似乎光就在眼前,伸手却无法捕捉一丝温暖。有时看似前面无光,却在绝望处看见有人手持蜡烛照亮了一个角落─身为基督跟随者的你我,是否看见黑暗的深渊?是否计算过与光的距离?在这当中,是否看见自己的责任?
註: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创作全见:完整十集剧本&幕后导读访谈记事,吕莳媛,公共电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