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那一次愛筵
文/晨小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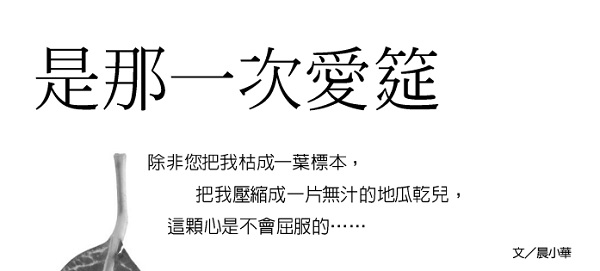
陣子,一顆流浪的心好疲倦,好想回台灣去。
其實,二十四年前勉強自己隨丈夫赴美時,心情已極為淒苦;從來,我就沒想要這麼遠離鄉土、拔根而去。臨走時孩子們的叮囑仍在耳際:「老師,學成速歸,不然我們要丟一粒中國的鵝卵石,飛越太平洋,K你,和師丈!」
而這一去就是十九年大漠平沙。我曾說,沒回過台灣,絕不去大陸;沒去過大陸,絕不遊香港;沒遊過香港,絕不到任何一個其它國家觀光。那一睹氣,竟真成就了我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心靈的放逐。我曾說,只是想看人,真的好想看人,想看看我故土的老友、師長和學生,想看看台北的電影街和書城,或是台灣任何一個角落、任何一個和我流著相同血脈的陌生人。從揮別植物園的清荷,到入定沙漠中的仙人掌,我的凝望已漸漸乾枯成一朵失根的蘭花。我說,我的神啊,除非您把我枯成一葉標本,除非您把我壓縮成一片無汁的地瓜乾兒,這顆心是不會屈服的⋯⋯
就在那段極度厭倦漂泊北美、思歸幾乎成病的時候,一席豐盛的晚筵,如明月般照亮了我心中的幽暗。
那是四年多前的一個冬日,我陪丈夫赴加拿大接受一個會牧職位的面談。波音737上,從冬陽燦爛的新墨州飛到冷颼颼濕搭搭的多倫多,我的心也冷冷濕濕地如沉谷底。神啊,您真的忍心讓我一個異鄉又一個異國地不斷漂流嗎?神啊,讓我回台灣吧!一路上我不斷向祂呼求。
當晚抵達後,一位弟兄把我們送到一個古舊教會的地下室,與一百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們共用晚餐。
那是一次奇特的餐會!狹窄擁擠的木板樓梯吱吱嘎嘎地上下著人群;半推半擠之下,我和丈夫跟著湧動的人群走進餐廳。一霎時,我驚住了,咱這隻來自阿布奎基的沙漠之鼠,二十年來沒未見過這麼多中國臉,更別說一下子見到這麼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!弟兄告訴我說,這十數年如一日、每星期五晚上查經班之前的愛筵服事,帶領了不知多少從未進過教會的人來認識了耶穌。弟兄說,這愛筵,是一位香港弟兄十多年來不聲不響的奉獻⋯⋯
我輕啜著小小保利龍杯內熱乎乎的豬骨湯,默默用塑膠叉子撥著紙盤中的醬油雞與燙青菜,一面默默望著那一張張風塵僕僕的臉以及一朵朵矜持含蓄的笑。弟兄說,這城市,每天都有不計其數的同胞從大陸過來,他們中間有些甚至是剛剛下的飛機⋯⋯是嗎?難怪我感覺他們面前似乎一個個擺著大盤大盤的東北餃子、天津包子或是大碗大碗的四川辣麵、紅油抄手⋯⋯
還能再堅持我基隆海濱的四神湯、以及台北街頭的蚵仔麵線嗎?一霎時,連兒時螢橋的星光與淡水河上的櫓槳,都愀然隱退而去,只耳際一個微聲清楚響起:孩子啊,妳若向靈裡飢餓的人發憐憫,使心中困苦的人得飽足,妳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升起,妳的幽暗必成為正午⋯⋯
是那次愛筵,那一次的愛筵使我回轉,讓我順服等候,讓一粒粒的「中國鵝卵石」,暫且在海洋深處漸漸堆起。


 作者小檔案
作者小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