輕鬆一下
文/劉晏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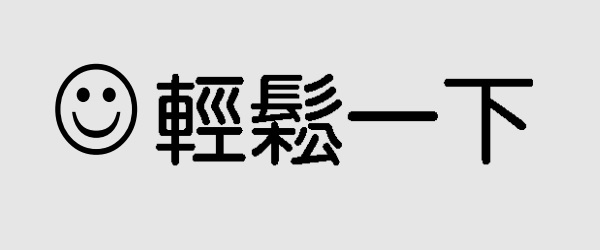
文字營期間,被蘇文安老師訓練眼觀四面,耳聽八方;感覺好像 Peter Parker 變成蜘蛛人,一切感官全敏銳起來。近視眼變透視眼、瘦雞變洛基(席維斯史特龍的那個Rocky)。但是,唉,生來一隻重聽的右耳還是沒醒來,還有我那「出類拔萃」的中文,製造了許多笑料⋯⋯
給我出糗的耳朵
培訓班報到的傍晚,大夥兒吃粽子喝蓮子湯時,俐理姊發了一張卡片,說是要寫給一位正在趕路過來的姊妹:「請大家簽一下這張卡片,Amy今天生病⋯⋯」我才吃完,正要出門溜達溜達,也沒聽完俐理姊之後說些什麼。回來後拿起卡片,洋洋灑灑寫了一句:“Please get well soon!"(請早日康復!)
終於,Amy,也就是月娥姨,拖著個小行李風塵僕僕卻精神飽滿地趕到。「她氣色很好嘛,沒什麼病容啊⋯⋯」我納悶著。忽然看到她右手包了一層黑黑的醫護棉套。是啦,大概是她手有什麼不適吧。晚上十點多後,課程結束了。俐理姊這時端出了一個生日蛋糕:「來,我們為Amy切蛋糕唱生日歌⋯⋯」不會吧!我嚇了一把冷汗,是不是把生日聽成生病了?慘了,人家好好的過生日我居然祝她早日康復⋯⋯唉,希望月娥大人不記晏君過,不要生氣囉!
請問「蟑螂」怎麼走?
培訓班結束後,我不自量力地自動升級上進深班。有一天要拍團體照,大家約好照相地點在倚著綠山坡、詩情畫意的修道院長廊。拍照時間快到時,瑞怡姊妹突然把我叫住問了一句:「蟑螂怎麼走?」什麼?蟑螂?「嗯⋯⋯」我歪頭很快地回想小時家裡的南美飛天蟑。「蟑螂這樣走⋯⋯」我縮著頭,張開雙腿雙腳,前後擺動走了幾步,一臉畏畏縮縮的齷齪樣。瑞怡大笑了起來:「我問妳長廊怎麼走,不是蟑螂怎麼走。」真是的,我這爛耳朵專給我出糗。
吃蠔油謝天恩?!
還有一次,藝術營的美學家們開結業畫展。我一眼就愛上了邱建勤弟兄畫的「天天有神恩」。鵝蛋黃的長玻璃窗前,有紅番茄、綠青椒、白糖糕、土番薯口味的棒棒糖在飛舞,四周一大群伴舞符號也加入這場盛宴,熱鬧快樂得不得了。我把邱畫家找來,請他為我解釋那些符號的意義:
「請問這是什麼?」我手指著三粒鈕扣問他。
「這是紅綠燈,感謝神保守我出入平安。」
邱弟兄操著一口越南廣東腔答道。
「那這個咧?」
「這個是房子,代表神給我一個溫暖的家。」
「噢,那這隻紅公雞是什麼意思?」
「嗯⋯⋯這是玫瑰花,不是雞。」
玫瑰花又代表什麼,我不敢問,把他的花看成雞已經很不好意思了。
「這又是什麼?」趕快轉移主題。他畫這三條彎彎曲曲的線,我看不大懂。
「WORO...」他咕嚕咕嚕地說。
「什麼?」
「WOOOOROOOO...」他又咕噥咕噥一次。
「蠔油?」我張大了嘴問。哇,邱先生實在敬虔,連有蠔油吃都要感謝神。
「唉,不是不是,這是猴揉、猴揉!他也大聲起來了。
「河流啦!」一旁的姊妹們都聽懂了。
停了一秒後,突然大家齊聲「哇哈哈哈」地彎腰捧腹大笑。
我笑得最大聲。
靦腆的邱弟兄笑得最小聲,大概是哭笑不得吧⋯⋯
我的破中文⋯⋯
培訓班圓滿結束了!一一向同學們道別後,我回到了在地下室的課堂。唉,怎麼時間飛逝得特別快?才跟大家熟稔起來他們就要走了。我意興闌珊地跌回平常坐的位子,順手拿起一本《人生補羹》開始翻了起來。唉,心裡又嘆了一聲。這些師兄師姊們的文筆真好真美,不僅故事真摯動人,還用了許多我看不懂或唸不出的字,像「迷迭」(我唸成迷史)、「婆娑」(我以為是婆沙)、(泂泂)〔我猜是回回〕之類的詞彙。如果文字營有畢業考的話,這一屆的總成績一定會被我拉下去,成為歷屆的笑柄⋯⋯
當然,同學們還是愛心滿懷地鼓勵我:「欸,妳的字跟我女兒的一模一樣耶!」(這位阿姨的千金好像是ABC。)
「妳給了我在美國教孩子中文的希望。」(那位媽媽搞不好以為我是在美國出生的。)
其實本人並不是黃皮白心的香蕉,而是臺灣土生、巴西長大、美國成熟的變種芒果,內外皆黃。平常大家稱讚我的中文好,是因為對我衡量標準太低。這次參加文字營,還往行李塞了一本梁實秋主編的英漢/漢英辭典,又厚又重。練習寫作時,全班都用原子筆,只有我一人用鉛筆,因為錯字太多,需要用橡皮擦。擦的時候,桌子搖搖晃晃;寫完後,橡皮屑又堆滿桌,同桌的同學們真是辛苦了。連小蘇助教(蘇老師的大公子)都抱怨:「妳可不可以不要用鉛筆寫?這樣很難拷貝清楚耶!」

